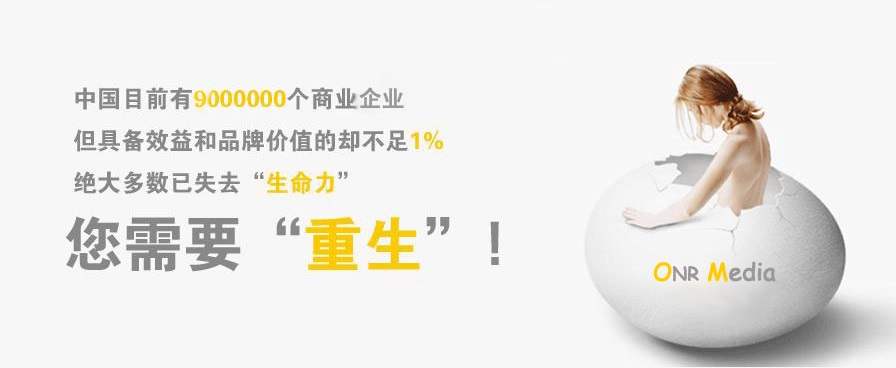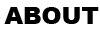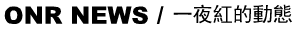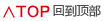《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度以其高額預(yù)售票房登頂中國文藝片的頂峰,又在極短時(shí)間內(nèi)急速墜落——其票房在2018年12月31日上映首日達(dá)到了2.67億,之后連續(xù)4天狂跌,分別為1130萬、186萬、129萬、26萬。
票房崩盤之外,同步的是豆瓣、貓眼等社區(qū)的評分直降,文藝青年大本營豆瓣對這部電影的評分是7分,但點(diǎn)贊數(shù)量最多的三條評論卻分別只給了2星、1星和0星;聚集了最多普通觀眾的貓眼評分則只有2.6分,在同期上映的各片中評分墊底(葛優(yōu)等主演的《斷片之險(xiǎn)途奪寶》為4.4分)。
觀眾與評論的怒火,還同時(shí)燒向了資本市場,元旦后開市第一天,《地球最后的夜晚》主要出品方華策影視遭遇跌停,市值損失16億。短短3天內(nèi),票房崩、口碑崩、市值崩的“三崩”滑鐵盧,令《地球最后的夜晚》成為中國電影史上最具戲劇性的個(gè)案。
平心而論,這部作品與近年來的大量爛片相比,肯定不是最爛的,畢竟全片精良的美術(shù)制作和導(dǎo)演畢贛的各種精雕細(xì)刻,加上湯唯、張艾嘉、黃覺等一眾明星認(rèn)真陪跑,這部片子絕對不是粗制濫造那一路。但為什么這樣一部作品,卻在市場上遭遇了巨大而特殊的“迎頭痛擊”呢?
很多人將主因歸于片方在前期營銷過程中,用“一吻跨年”和暗示有性與情色內(nèi)容的劇照來誤導(dǎo)觀眾,導(dǎo)致許多想以這部片子來作為“情趣序曲”的小情侶們在一頭霧水之后怒而踢館。我倒是不太相信趕在12月31日去看片的觀眾都是準(zhǔn)備看完電影去曖昧的,事實(shí)上,這部片子確實(shí)上演在一個(gè)極為特殊的時(shí)刻——近十年來,國人第一次如此高度一致地急于告別2018年,希望快快進(jìn)入2019年。估計(jì)相當(dāng)一部分抱著這種想法的觀眾走進(jìn)影院時(shí),都想通過一年“最后的夜晚”來結(jié)束過往,走進(jìn)新的溫暖與希望。
這種希望和期待,對于一部跨年電影作品而言本來可以算是“天時(shí)”,但對《地球最后的夜晚》而言,卻是“災(zāi)難”。不論是對于普通小鎮(zhèn)青年或是一線城市略喪的白領(lǐng)精英,還是所謂的資深文藝中青年,這部片子都絕對不是讓你感到輕松、溫暖甚至治愈的作品。恰恰相反,在長達(dá)2小時(shí)20分鐘的漫長時(shí)間里,斷裂、破碎、囈語式的現(xiàn)實(shí)與夢境交織在一起,黑得能讓人看瞎的用光和剛有點(diǎn)頭緒又瞬間失焦的敘事,很容易讓人感到壓抑煩躁。我自己在隨著劇中男主(不得不)拿起3D眼鏡戴上,并明確地知道后面還有70分鐘的片長時(shí),內(nèi)心真的是崩潰。
中國實(shí)驗(yàn)戲劇的扛旗人林兆華先生在近十幾年的排戲過程中,最經(jīng)常講的一句話是“說人話”。這句話對戲劇有用,對電影也一樣。《地球最后的夜晚》劇中人物,幾乎沒有一個(gè)是好好說人話的,所有的臺詞,都像是日積月累抄在一個(gè)發(fā)黃筆記本上攢下的“文藝金句”,被一攬子強(qiáng)行安插在各個(gè)人物身上,并以極做作的方式念出來,除了那個(gè)打乒乓球的小男孩,他幾乎是全片唯一沒有被污染的表演者了。被各種營銷文案包裝的3D長鏡頭在技術(shù)上或許可圈可點(diǎn),但于全片整體敘事并無幫助,從頭至尾暗沉的用光、重復(fù)的鏡頭語言和長廊視角,令人昏昏欲睡。
因?yàn)闋I銷過度而丟掉普通觀眾的好評、后續(xù)票房斷崖式下跌,是預(yù)期透支后大眾市場的反制與糾偏。但如果僅僅只是“撈過界”或是普通觀眾看不懂,“地球”的結(jié)局可能還不致如此。如果自身功底過硬、業(yè)界精英和意見領(lǐng)袖能夠基本認(rèn)可,仍有機(jī)會不斷通過正面評論和深度講解影響觀眾,并最終達(dá)成某種平衡。但正是因?yàn)槠幼陨淼膯栴}重重,評論界和業(yè)界也不斷“補(bǔ)刀”,“地球”同時(shí)也很快失去了文藝片的基本盤,使得它在輿論和票房兩條戰(zhàn)線上,都很難再翻身了。
長久以來,文藝片在國人心目中還是保有了某種神圣性的,似乎冠之以“文藝片”就有了某種高人一等的神性,也有了讓你看不懂的權(quán)利。但事實(shí)上,在多樣性日益豐富的電影市場上,中國觀眾整體的視野已經(jīng)在不斷擴(kuò)大,審美和判斷力都在快速成長,不再會因?yàn)槟硞€(gè)單一因素而買單,導(dǎo)演、演員、編劇、類型或其他因素,最終都只能是綜合分中的一項(xiàng)。不論前期電影宣發(fā)階段媒體和營銷方如何造神,等片子真正上市之后,市場和觀眾還是有機(jī)會展現(xiàn)自己的觀點(diǎn)和意志。
馬克斯·韋伯在研究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中,認(rèn)為理性化過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或“除魔”,即把一切帶有“巫術(shù)”性質(zhì)的知識或宗教倫理實(shí)踐要素視為迷信與罪惡,加以祛除。《地球最后的夜晚》這次前期沖頂和高臺跳水的軌跡,不過是一次加了倍速的“造神”與“祛魅”,也正因?yàn)檫@種加速,從而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shí)與市場的戲劇性。
#p#分頁標(biāo)題#e#這一案例對于未來中國文藝片的發(fā)展,是會有一定負(fù)面影響的。因?yàn)樵诋?dāng)今電影市場仍由商業(yè)和資本主導(dǎo)的大勢之下,如果不斷有好的文藝片突圍而出,形成另一種成功案例和“賺錢效應(yīng)”,會促使中國電影的投資格局出現(xiàn)更多可能性。但一部任性的失敗之作,很可能在一段時(shí)間之內(nèi)讓大家對這個(gè)方向避而遠(yuǎn)之。
試想,如果這部片子不是在一開始就爆得大名,而是從小眾開始,因?yàn)榭诒逆準(zhǔn)絺鞑ザ窖菰綗幔纬傻烷_高走的反轉(zhuǎn)之勢,最終達(dá)到2.8億元的高額票房,那《地球最后的夜晚》在中國電影史上書寫的就是另外一個(gè)神話了。畢竟此前在柏林電影節(jié)斬獲金熊獎(jiǎng)的《白日焰火》,票房也只有1.02億。希望未來我們能夠看到這樣的文藝片神作在中國市場上出現(xiàn),洗刷一下“文藝片就等于看不懂”的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