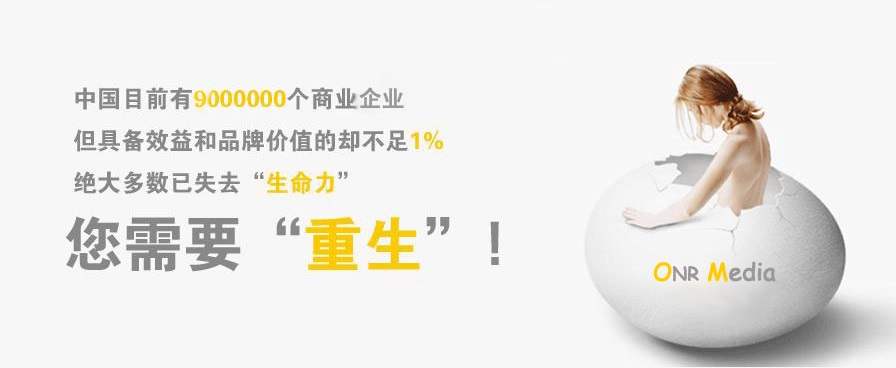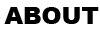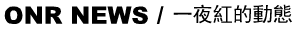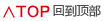沉默,會是個有效應對危機的手段嗎?想必大多數人不會同意。
尤其那些受過西方危機公關理論教育的管理者們,耳邊總是容易響起那句在這樣的時刻反復被提及的話“說真話,而且要在第一時間說”。大家都篤信這一信念,以為在信息爆炸的這樣一個時代,不是在關鍵時刻爆發,就得在沉默中死亡。無數成功的案例似乎印證了這一思路的正確性。在一件事情被質疑的時候,出來說話的企業容易被視為是負責任的,如果態度誠懇,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負面因素的作用,進而得到公眾的好感。所以,大家總是毫不懷疑地認為,話語和行動永遠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而沉默,則是死亡的前兆。
人,總是習慣為自己相信的理念尋找證據,而對同樣存在的反例視而不見。

請點擊輸入圖片描述
當年郎咸平炮轟國企,幾乎稍有知名度的企業都不能幸免,所謂的三叩TCL、四問海爾、七敲格林柯爾,為其典型代表。然而炮火過后,為何有些企業安然存活,有些卻從此一蹶不振,逐步陷入山窮水盡的境地?
是否有人思考過這與沉默之間的聯系?
當然我們不能從顧雛軍當年與郎咸平的激烈論戰并最終被訴之于司法程序中,簡單導出格林柯爾后來的命運。但這樣的激烈對抗,和對話語權的堅定信念,卻毋庸置疑地給格林柯爾帶來了不少麻煩,最后連顧雛軍本人都搭了進去。
古語有云:“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蘇軾的話即使放到今時今日,也不乏其先見之明。
格林柯爾面對郎咸平的質疑,怒目相向,拍案而起,竭盡全力去辯白反駁,還將郎訴至法院,一心只想爭回一口氣。然而即使最后戰勝了又如何?企業身陷其中,當事人的言詞,真的能贏回公眾嗎?君不見,當時網上負面論調所居之多,甚至謾罵不斷,導致股民的情緒高漲,媒體也恨不得把火越燒越大,在這樣一個非理性的情境中,哪怕是蘇格拉底出來說話也未必有人會聽,何況是一個因受指責而被置于審判席上的當事人?面對一幢即將倒塌的大廈,迎頭而上卻不知退而求全,不是勇敢。
更重要的是,不知他們在起訴時有沒有想到過,這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那些同樣受到指責的企業的衛道者,不自覺地成為了他們的英雄。郎咸平的指摘,并不是針對一家一戶,而是以國企改革為背景的分析,掃蕩范圍無限廣泛。既如此,倒不如把它當成龍卷風,勢頭雖強,終不能持久,只要咬咬牙,頂住這一陣,等到風刮去下一家去時,一切又都風平浪靜了。孤身奮戰強勢的龍卷風,阻礙它對競爭對手的迫害,那是救世主的使命,卻不該是商界中作為個體的企業的理智選擇。
通過上述分析,想必這時候再提出沉默于解決公關危機的重要作用,便不該被置疑了吧。
當企業沒有致命的質量問題,或者也談不上在遭遇嚴重品牌危機,而只是遇到了一些來自社會方面不同聲音的質疑時,企業必須作出一個預計,即是否應該給予回應和以什么樣的方式回應。
發表聲明并非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劑良方。
沉默或許會令人難堪,或許得讓一向大權在握的管理者們忍氣吞聲,但從利弊衡量的角度,沉默確實能夠使企業利益最大化。更何況,此時的沉默,并不就是指無所作為,而僅僅是指在對外行動上隱忍的一個方面而已。因此,無論是韜光養晦的蓄勢待發也好,是退避三舍委曲求全的自保也好,總勝于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壯烈。畢竟,建起一幢大廈并不容易,而要毀掉它,只在瞬息之間,掌握生殺大權的決策者們,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從另一個角度,企業的沉默其實應該與其前期的不沉默相結合,即企業前期如果信息足夠公開,自己主動說,則勝于最后沉默,也更勝于被動去說。
首先,企業沒有重大的產品質量等實質性問題,而只是其他方面的問題使品牌受到威脅時,企業的決策者預計闡述的解釋將對抗大多數的公眾情緒(包括消費者情緒、股民情緒等),則可以保持沉默。
其次,當企業解釋的理由與媒體報道的方向不一致,而二者能很清楚地分辨出誰是誰非的問題時,企業處于弱勢時也應該保持沉默。
如某電子學習產品,夸大了其功能與效用,被一家報紙質疑后,如果高姿態迎戰,結果學生知道,家長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企業的產品將有走向衰亡的危險,同時給媒體連續報道創造了機會。
對此,上上之策為:將夸大的廣告宣傳默默收回,當一階段“啞巴”。
第三,當行業專家的解釋對企業不利,而企業也無法找到強有力的反駁證據時,企業也應該保持沉默。
比如,當經濟學家的分析對企業不利,而企業無法找到充分的證據為自己辯解時,企業也應該選擇沉默。
這里面還包含深層次的理性的選擇的要素,復習一下哈耶克的論斷:
“一個物理學家,即使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也只能影響本專業的物理學家。而經濟學家則主要影響外行:政治家、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公眾,大眾消費者。”
許多案例表明,在特定情勢下沉默是最好的選擇,沉默能夠幫助企業抵擋暫時的危機乃至避免更大的危機。
當然,沉默策略的基礎是:企業自身沒有過錯,在情況復雜的時候保持沉默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和麻煩,否則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