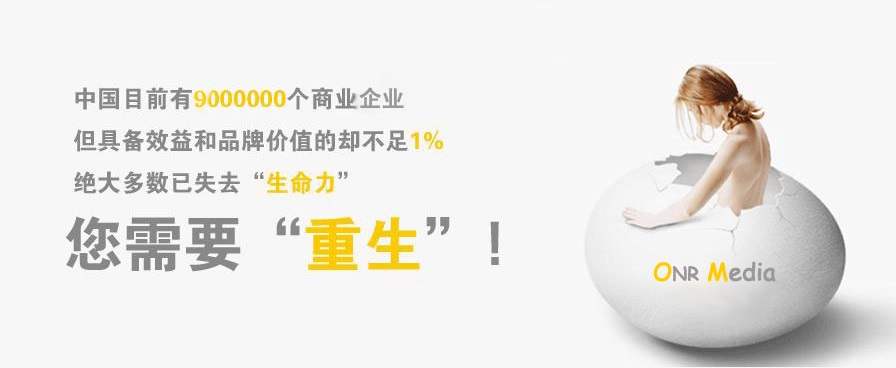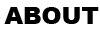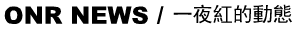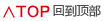有句古話“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歷經(jīng)千百年,傳遞“壞事”的方式已經(jīng)從口口相傳,變成了各種媒體——電視、廣播、網(wǎng)站、手機APP,而傳播的能力已經(jīng)不是古人想象力里面千里的極限,如今,幾乎在一瞬間,一個聲音就能傳遍全球。而這個古人口中的“壞事”,也被賦予了現(xiàn)代的意義——“公關(guān)危機”。

反過來,如果給現(xiàn)代的“公關(guān)危機”一個定義的話,那應(yīng)該就是通過各種媒體傳播的那些“壞事”,對于企業(yè)可能是出產(chǎn)的手機爆炸,也可能是汽車的發(fā)動機漏油,生產(chǎn)過程中對周圍環(huán)境的污染,對自己員工福利的蔑視;對于個人可能是歌手抄襲作品,明星婚內(nèi)緋聞,政客不擇手段等等。

公關(guān)危機的“主”、“客”構(gòu)成
如果想要把握一件事,我們首先要理解它,如果想要理解一樣?xùn)|西,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對它進行拆解,去觀察構(gòu)成其主要的成分,就好比研究鐘表總歸是要拆開它。
那么公關(guān)危機這個黑匣子怎么拆開?借用古語中“壞事傳千里”的模式,實際上一個公關(guān)危機,核心有三個要素——誰的危機?什么危機?誰知道了這個危機?這三個要素構(gòu)成了危機的“主客”關(guān)系。

“主”就是危機的主體,一般來說,都是具有一定的公眾知名度的主體,比如隔壁老王就不太能夠成為一個危機的主體,除非他是個大明星。基本上危機主體分為兩種——個人和機構(gòu)。個人就很清楚了,,是具有社會知名度的偶像、藝人、專業(yè)人士(知名的醫(yī)生、律師、匠人、主持人、政客等等)。
而機構(gòu)就會比較復(fù)雜,有現(xiàn)代型的企業(yè)法人組織,也有公益、非營利的機構(gòu);有民間社團,也有政治團體;更有可能是某一職業(yè)群體或者城市、國家等等(比如教授這個群體,漸漸被“叫獸”污名化了)。

“客”就是危機的客體,就是那些親身經(jīng)歷或者看到、聽到、了解到危機,并且對危機做出反應(yīng)的人或機構(gòu)。他們有可能跟危機的主體有直接關(guān)系,比如是發(fā)生危機公司的員工,或者股票市場中該企業(yè)的投資人;也有可能有間接關(guān)系,比如是該公司產(chǎn)品的消費者,該公司的上下游供應(yīng)商;更有可能是跟這個公司毫無關(guān)系的旁觀者,但是他們接收信息之后,發(fā)表自身的意見,不斷向外傳播,而形成了一種危機的中介。
通過這樣的分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危機公式,“公關(guān)危機=主-危機-客”。接下來,我們就需要了解——
當(dāng)危機發(fā)生的時候,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舉個簡單的例子,前些日子,某豪華品牌的汽車發(fā)動機漏油,消費者維權(quán)的信息引起了廣泛的關(guān)注,這個危機中,環(huán)節(jié)眾多,內(nèi)容蕪雜,但我們可以利用剛剛得到的危機公式,想要了解危機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實際上就是了解在危機作用之下,“主客”之間發(fā)生了什么,或者更簡單的來說,是客體對主體的危機產(chǎn)生了什么反應(yīng)。

當(dāng)發(fā)動機漏油事件剛剛發(fā)生的時候,實際上該豪華汽車品牌陷入了一場——信任危機。也就是觀眾們會質(zhì)疑該品牌的車不夠好,這是其一;質(zhì)疑該公司管理有漏洞,這是其二;質(zhì)疑該公司的經(jīng)營誠信有問題,這是其三。
但這只是個表面的反應(yīng),更深層次去探究,該品牌實際上陷入了一場——“意義危機”。這涉及很多知識背景比如符號學(xué)、認知論等,但簡化來說,我們理解一個事物、一個人并不是直接去理解他們,而是通過一些關(guān)鍵詞的詮釋。比如我們說一個人,腦海中會浮現(xiàn)他的形象,也會響應(yīng)出他的一些關(guān)鍵詞,比如靠譜、幽默、健談等等。

在商品社會,這種意義的聯(lián)結(jié)更為明顯,比如我們提到快餐會想到麥當(dāng)勞肯德基,提到麥當(dāng)勞會想到選擇和歡笑,提到汽車會想到奔馳寶馬,提到奔馳會想到低調(diào)豪華等等。這種聯(lián)想,也被成為“品牌印象”。這是很多企業(yè)賴以生存并引以為傲的資本,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排名,說某某企業(yè)的品牌價值為多少億,本質(zhì)上,就是這種聯(lián)想的關(guān)聯(lián)體系價值。
而在“信任危機”背后,就是發(fā)生了這種“意義危機”。那個豪華車品牌曾經(jīng)的品牌聯(lián)想,包括豪華、可靠等意義,在危機的沖擊下動搖了。危機的觀察者通過對危機現(xiàn)象的理解,重新得出了結(jié)論,這個豪華品牌的品質(zhì)不可靠、經(jīng)營不誠信等,這種意義被賦予在這個品牌的周圍,甚至在短時期內(nèi)形成了第一聯(lián)想。

當(dāng)然這個“意義危機”并不是最可怕的,雖然對品牌價值帶來了損害,但公關(guān)危機最大的能量則是第三個階段的“信用危機”。也就是對于該豪華品牌,無論你說什么,消費者、觀眾都不信。原來僅僅是對品質(zhì)的質(zhì)疑,最后演變?yōu)閷τ谄放频娜P否定。
再拿一個例子,比如某個藝人被爆出軌。最開始是“信任危機”,人們不再相信他在道德層面的模范作用;慢慢的會轉(zhuǎn)向“意義危機”,他好父親、好丈夫的“人設(shè)”崩塌了,意義的關(guān)聯(lián)重新被打亂分配;最后發(fā)展為“信用危機”,也就是這個藝人說什么都不值得信,他的一切都是有問題的,他的作品也不應(yīng)該被欣賞。
所以,我們可以將危機的發(fā)展總結(jié)為另一個發(fā)展公式——危機=信任危機->意義危機->信用危機。

危機之中,沒有萬能的解決鑰匙
對于公關(guān)危機的解決,被稱為“危機公關(guān)”。在社會上流傳著很多解決的模式、模板、模塊化方案,也有很多危機公關(guān)的大師存在。但本質(zhì)上,就像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一樣,也沒有兩個相同的危機,以及兩個相同的危機解決方案。經(jīng)驗的價值并不體現(xiàn)在解決危機的結(jié)果,而是在于對于危機程度的判定和客體心理的把握上。再根據(jù)這些判斷,去尋找解決的最優(yōu)路徑,也許一條,也許幾條,但總的來說,沒有萬能的解決鑰匙,更沒有那個唯一的最佳答案。
根據(jù)公關(guān)危機發(fā)展的階段,以及給客體帶來的心理上的影響,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向選擇——
信任危機:澄清輿論or 承認錯誤
在危機的最初階段,或者說影響程度最小的階段。個人或組織面臨的往往是危機“觀眾”對于某一些方面的質(zhì)疑。這時候要做的就是在信息收集、分析和評估之下,來去確定,“觀眾”所了解的信息是否為真實的。
如果“觀眾”了解的信息不夠真實,就需要去澄清。比如明星經(jīng)常會發(fā)聲明,澄清一些八卦。當(dāng)然做這個動作的前提是打鐵還要自身硬,身正不怕影子歪。一旦聲明出去,就要面對更嚴苛的輿論審查,比如那個翟姓演員,對自己學(xué)位的自信澄清,反而遭到更深的挖掘。

如果“觀眾”了解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自身本來就有些問題,這時候,最好的辦法往往不是逃避,而是承認錯誤。當(dāng)然,承認錯誤,也是有技巧的。舉個例子就是“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承認錯誤的時候,一定要尋找那個對自己傷害最小的錯誤進行承認。通過承認這個動作,引起“觀眾”對于自身態(tài)度的認可,盡快度過輿論風(fēng)暴。
在這個階段,唯一不能做的,就是硬扛,危機有一萬種對的處理辦法,但只有一種錯誤的辦法,那就是——硬扛了。
意義危機:重建or 阻斷
當(dāng)危機持續(xù)深入,從質(zhì)疑轉(zhuǎn)到對原有意義的損害時,這場戰(zhàn)役就升級了。人們對于某個企業(yè)的聯(lián)想,從可靠轉(zhuǎn)變?yōu)榭尚Φ臅r候,簡單的信息澄清、道歉、整改都已經(jīng)不能夠起到關(guān)鍵作用了。
這時候,危機的主體,需要做一個判斷,一個選擇,一個比較,一個戰(zhàn)略上的新決策。那就是對于以前在“觀眾”心中的那個意義聯(lián)結(jié),是投入重金,去堅持,去重建;還是及時的放棄,阻斷這個意義,避免危機的持續(xù)蔓延,同時尋找新的意義并賦予自身的意義體系。

這就像一次出軌問題之后,夫妻究竟是該重修舊好,還是當(dāng)即離婚一樣的抉擇。沒有百分之百的正確,都是在一種衡量和取舍之間來找到更合適的道路。堅持原有的意義,有的時候是不得不做。
比如此前的牛奶危機,很多企業(yè)如蒙牛、伊利在危機之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重建人們對于牛奶品質(zhì)的意義信任,這個是無奈之舉,因為牛奶以及食品這樣的產(chǎn)品,品質(zhì)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排他性的第一位。也就是說沒有了品質(zhì),其他的意義再豐富——比如營養(yǎng)齊全——都沒有價值,人們都不會選擇。

而阻斷則是一種止損,一種對“沉沒成本”的快速舍棄。當(dāng)然前提是受到損害的那些意義、價值并不是核心的、必不可少的。比如某個年少明星被抓到抽煙,這時候可能就要及時阻斷此前青年模范的人設(shè)打造,慢慢的轉(zhuǎn)向成年人世界,同時賦予自己新的人設(shè)標(biāo)簽,比如真誠、直爽等。在阻斷之后,一定要賦予新的內(nèi)涵,否則真空的位置始終是個傷疤,沒有義肢的傷口永遠都會讓人聯(lián)想到那場事故——危機會不斷地被重提。
信用危機:改頭換面or 重新培養(yǎng)
如果真的危機一發(fā)不可收拾,到了信用危機的階段。很多時候危機的主體就難以自主選擇做什么了,大多都會陷入一種迫不得已的境地。就如“三鹿”這個品牌永久的消失在我們視線中一樣,有時候只能選擇隱姓埋名,相忘于江湖。就算想要重出江湖,也要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當(dāng)然,有時候放棄可能是最輕松的選擇了。大多數(shù)情況下,危機的主體都不得不背負著一種“污名”,繼續(xù)的向前走著。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的重新培養(yǎng)跟“觀眾”之間的關(guān)系,不斷地試探著人們對于某些意義的記憶,不斷地試圖重新拿回自己的曾經(jīng)的榮耀。在這個過程中,耗費掉了大多數(shù)人和企業(yè)的意志,也僅有極少數(shù)的人能做到知恥而后勇,反敗為勝。

再回到一句古話“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有些危機是很多偶然因素疊加的不可預(yù)知的事故,但大多數(shù)危機都是個人或機構(gòu)挑戰(zhàn)社會道德、文化、價值觀行為之下的結(jié)果。所以防患于未然,永遠是最好的辦法,不斷監(jiān)視自身,一日三省,方能高枕無憂。